今年是伟大的德国文学家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诞生270周年。今天,阅读歌德,纪念歌德,有没有“过时”?
歌德的生命智慧和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丝毫不亚于他的著作。他不应该只存在于文学史中,成为一个象征符号。现代人完全可以把歌德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精神导师来亲近,以他为镜,自我修养,自我映照,在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奋进。
——编者

歌德画像
一尊“半神”
“谁若仅懂得文学,就对生活知之甚少”
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,歌德都是德意志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、无可比拟的人物,他属于“一次性”的天才现象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歌德当然首先是超凡脱俗的世界级诗人,他一生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。无论何时何地,歌德总能即兴赋咏,信手拈来皆是“诗”。歌德在诗里吸饮纯洁生命的欢悦和痛苦,但他血液里除了奔腾荡漾的诗兴,也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,那就是对现实客观的注目。“诗既美又善,但它无法引导生命。谁若仅懂得文学,就对生活知之甚少。”这是歌德的文艺观,也是生活观。歌德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诗人和世俗生活并不相悖。尽管他承认,他真正的快乐来自“诗意的冥想与创作”,但我们知道歌德的“副业”不止一桩,且都是他主动的选择:他是殚精竭虑的宫廷枢密顾问,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学研究者,乐趣无穷的生活家和收藏家,以及,无可否认的:歌德也是一生恋爱无数的情圣。如果说浮士德代表着歌德形而上的一面,那么梅菲斯托就是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。歌德是极少数把灵魂与肉体、精神创造与世俗生活融合得极为高明的幸运者。
歌德在他所处的时代,就已被视为圣哲,被奉为“半神”。青年歌德的丰神俊朗、活泼狂野,令无数男女为其风采才华倾倒;25岁,少年维特横空出世,一句“我返回自身,发现了一个世界”,让世人耳目一新!不必说18岁的魏玛大公对歌德爱慕有加,一生厚待,就连拿破仑也不甘落后,声称自己至少读过七遍“维特”;中年歌德堪称“当世大儒”:博学多才,沉稳优雅;他携手青年席勒,把德国文学推向巅峰时代,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;老年歌德俨然如“国王”,沉默寡言,威仪万千,令人膜拜又令人畏惧,是思想的丰碑亦是新生力量的障碍,以至于1832年歌德逝世之后,整个德国知识文化界沉浸于悲伤的同时,也大大松了一口气:一个漫长的“歌德时代”终于结束了。
想当年,魏玛妇女广场边上那栋花园房子,曾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整个世界的目光,多少同时代人把争取到歌德的关注视为幸福和荣耀。如果要定义歌德与他的时代的关系,我们可以说:18世纪造就了这个天才,而这个天才又以“令人感到玄妙的,先知般直觉”(托马斯·曼语)预言并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。那么,在歌德诞生270周年之际,在时代气质和世道人心早已几度沧海桑田的今天,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歌德,纪念歌德?他对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有何指导意义?换句话说,歌德有没有“过时”?
德国著名学者、传记作家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给出了令人心动的回答。萨弗兰斯基认为歌德“不仅以其著作,而且也以其生命而令人振奋。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作家,而且是个生命的大师。两者合一,让他对后世来说,成为取之不竭的源泉……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机会,以歌德为镜,更好的理解自身和自己的时代。”萨弗兰斯基于2013年推出了可作为其创作巅峰标志的传记《歌德:生命的艺术品》(Goethe:Kunstwerk des Lebens)(三联书店于2019年5月首推中文版,书名为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,译者为卫茂平教授)。萨氏怀着郑重爱戴的态度,使用的却是一种轻盈流转的笔法,把这尊高高在上的“半神”重新拉回到人间,让读者见识到一个丰富的、真实的个体生命是如何一步步自我启迪、自我建构、自我完成的。在笔者看来,歌德的生命智慧和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丝毫不亚于他的著作,现代人完全可以把歌德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精神导师来亲近,而不应该只让他存在于文学史中,成为一个象征符号。

天生我材
“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,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”
不知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:“爱自己往往是一个传奇式生活的开端”。这里的爱,并非是自我迷恋,它意味着对自我生命的强烈认同和深刻关注,意味着一条富有创意、并且被一种超人的意志和责任感引导着的自我发展之路。歌德对自己的“天分”是有高度自觉的。在31岁时写给年长八岁的苏黎世友人拉法特尔的信中,歌德有这么一番自我预言:
“将我此在的金字塔——其根基我生来就有,为我建立——尽可能高地插入云端,这个欲望压倒一切其他,不允许哪怕是片刻的遗忘。”(引自 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扉页献词)
歌德终其一生都不曾遗忘这份“造塔”使命。他孜孜不倦地建构着自己,并把“造塔”的过程一一记录,以示世人。托马斯·曼曾言:“歌德是最完美意义上的教育家式的人。他一生中两部纪念碑般的作品《浮士德》和《威廉·迈斯特》是教育诗篇,是人的教育培养过程的展示。”相较于我们对莎士比亚生平的一无所知,歌德的全部作品都具有自传色彩。维特、浮士德、威廉·迈斯特个个都有他的分身和影子,而《歌德谈话录》《诗与真》以及浩瀚的书信札记让歌德的形象乃至他内心生活的种种都得以“复活”。
通常,在世人眼里,歌德可谓顶级“人生赢家”:家世优渥,仕途顺遂,高朋满座,四海驰名。歌德身上还有令世人艳羡的一点:歌德爱过许多人,也被许多人爱:兄妹之爱,知己之爱,恋人之爱,家庭之爱,师徒之爱。他的一生是被“爱”引领着、开拓着的一生。“爱”与他的创作和生命连成一体。歌德有诗云:
我们源自何方?
源自爱。
我们缘何迷失?
匮乏爱。
是什么助我们超越?
是爱
我们如何找寻爱?
凭着爱。
我们何故长久哭泣?
因为爱
我们何以结成同心?
因为爱。
(黄雪媛 译)
爱成就了歌德,助推了他的天才之喷薄。但我们不要忘了,歌德的一生也是辛劳的一生。老年歌德有一回向他的秘书艾克曼博士倾吐:“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,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,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,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。我可以说,我活了75岁,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。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,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。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。”(引自《歌德谈话录》,朱光潜译)。这番话是对他25岁时写下的那首《普罗米修士》的一个遥远的回应:
宙斯,要我尊敬你,为什么?
你可减轻了
任何重担者的痛苦?
你可遏止了
任何受威吓者的眼泪?
把我锻炼成人的
不是全能的时代
和永恒的命运吗
它们是我的也是你的主人!
(冯至 译)
显然,歌德是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士了,他自动背负了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使命,沉浸其中,去受苦,去哭泣,去享受,去欢乐。“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,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。”
直到他生命结束前的半年,82岁的他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求新的素材,新的自我。在歌德的时代,正是“天才”之说流行的时代。康德明确肯定“天才”的存在:“在一切艺术之中占首位的是诗,诗的根源完全在于天才。”歌德的可贵之处在于,他一方面完全明白自己犹如缪斯的宠儿,注定会名垂青史,另一方面又不忘训导年轻人,天才的养成要依赖勤学苦练。在他的生命接近尾声之际,歌德对“天才”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,他对艾克曼说:“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,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……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,就连最大的天才,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,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。”歌德身为巨人,庄严自持,又兼虚怀若谷,清醒自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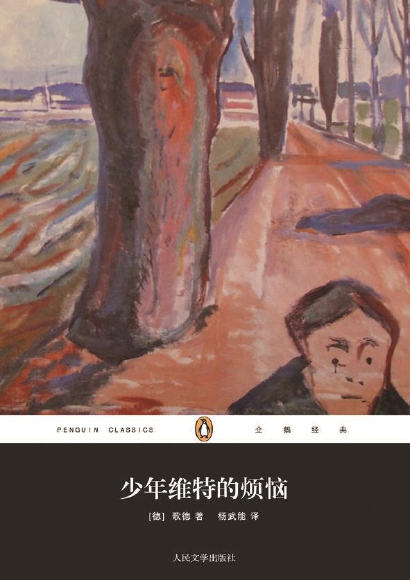
知足不殆
“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”
在歌德留下的格言诗和谈话录里,我们常常读到他对“理智”的重视和对“适度”原则的主张。这两样也是歌德保持健康、长享盛名的秘诀,正所谓“知足知止,知足不辱,知足不殆”。譬如,他认为雨果是“过度多产”:“他那样大胆,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,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,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!”再譬如论及“自由”,歌德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,从事本行的工作就够了。他甚至认为对自由理想的过度追求害了席勒,导致席勒身心耗竭,断送了性命。我们可以想象歌德说此话的时候心里该有多么遗憾。席勒应该是歌德一生中唯一智力上“势均力敌”的朋友,生得比他晚,却死得比他早。十年亲密相处,如琢如磨,如切如磋;如今故人音沉响绝,歌德难免有种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孤独。即使后来歌德又有了策尔特这样的密友,也难以填补他失去席勒的空白。在席勒去世20年后,歌德有一个惊骇之举:据说他悄悄把席勒的头盖骨带回,放在自己的书房里,朝夕相对,长达一年。
歌德年轻时恃才傲物、一骑绝尘,随着年岁增长,岁月安稳,他性格中市民性的一面日益凸显。他越来越讨厌偏激的观点,暴力的行为,连带着不认同剑走偏锋、愤世嫉俗之人,比如拜伦,比如贝多芬。歌德惊叹拜伦的非凡才能,认为在创造才能方面,世人无一能与拜伦争锋,“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。”但是他对拜伦的性格却不以为然。歌德痛惜拜伦的早陨。他认为拜伦跑到希腊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,是“对世界的误解”。
歌德像是一颗星辰,围转着自己的重担,最大的任务就是“完成自己”。为此,他树立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,如萨弗兰斯基所言:“一个精神和灵魂免疫系统”。他只去接受他所能应付的世界,而对于他无法理解和无法接纳的一切,就排除在自己的生命圆圈之外。
歌德追求的是“平衡”和“建设”。对于世界的好与坏,歌德主张不必为坏事伤心,而只去永远做好事。“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,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。”

歌德《浮士德》插图,弗朗茨·史塔生绘
格物致知
“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”
“你若要为全体而欢喜,就必须在最小处见到全体。”对歌德而言,坐在一棵树下乘凉,而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,不去了解它需要什么样的生长环境;赞美蓝天白云,却不寻思天空的蓝色缘何而来,云朵的形成是什么原理,这都是不应该的。鸟兽虫鱼,皆有命名,天地万物,皆有其理。既要知其然,又要知其所以然。大自然是细节构成的王国,所以歌德主张:“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”。歌德一向贬低那些沉溺于主观情绪而忽略现实细节的诗人。
歌德的文艺观念既受古希腊传统的滋养,又得到现实主义的支撑,他的艺术探寻之路就是一条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之路。
因此,歌德是这样一个兼具诗性和科学性的自然之子。他既能写出《荒原小玫瑰》这样清新伤感的少年爱情,《浪游者夜歌》这般返璞归真的生命感悟,也能写出研究植物起源与变形的著作《植物变形学》,他还著有《实验论》和《色彩学》,甚至还有一项重要发现,即证明了人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颚间骨。歌德对知识这种广采博纳的态度和孜孜以求的钻劲,也使他能胜任各种工作。在魏玛辅佐大公的生涯里,歌德先后担任的职位列出来有一大串:枢密顾问、矿物官、**部长、财政部长、建设部长、剧院监督。工作的繁琐沉重,自然夺去了歌德大量文学创作的时间,但也赐予了歌德一笔财富:务实谨慎,不虚妄,不浮泛。“你若要迈入无限,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。”
遗忘之术
“不管作为园丁或者农夫,作为猎人或者矿工,这种认识都会让我们摆脱自身。”
如果说,不与对手纠缠是歌德的处世之道,那么“遗忘之术”是他保全自身的生命策略。在安适的表象下,歌德其实经历过多次危机,不止一次差点精神崩溃。幸运的是,他天性中的“遗忘之术”,一种“断念”的本领,能帮助他化险为夷,重整旗鼓。有时,他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遗忘,有时,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科学研究工作,或则不失时机的“逃遁”,比如逃去意大利隐居两年,休养生息,韬光养晦;他甚至借昏睡或大病一场,抛弃过去,割断关系。
但谁要是
心已被不幸扼住,
他想挣扎着
反抗铁索的羁绊,
就会徒劳无功。
只有那锐利的剪刀
最终能将他斩断。
(卫茂平 译)
第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歌德唯一的妹妹科尔内莉亚亡故之际。兄妹俩感情深厚,科尔内莉亚把年长一岁的哥哥看作是理想男子的标准,他们习惯分享彼此的思想和情感。妹妹的婚姻阻隔了彼此,婚后的科尔内莉亚竟失去了生活的兴味,渐渐枯萎下去。妹妹的死讯传来之际,也恰恰是歌德在魏玛春风得意之时。歌德形容妹妹的离世“仿佛将他维持在地球上的强大根系掘出”,他第一次经受了生命悲苦的考验。他在风雪交加的天气里策马独行,隐姓埋名,前往哈尔茨山,去寻找那把“锐利的剪刀”,把自己的悲伤斩断。“只有借助自然,才能从一种痛苦的,自我折磨和阴郁的精神状态中获得拯救和解放。不管作为园丁或者农夫,作为猎人或者矿工,这种认识都会让我们摆脱自身。”他在哈尔茨山拜访了矿洞,让人手持火把带着他匍匐穿行于黑暗的矿道;之后他又不顾危险,冒着冰雪登上布罗肯峰,去接受自然神秘之力的命运启示。登顶后,歌德写下这样的诗句:
神秘而又坦荡,
你带着未经探索的胸怀
立于惊愕的世界之上。
从云端俯瞰
它的辽阔和辉煌。
你以自己身边兄弟的血脉
将它浇灌。
(卫茂平 译)
冬日哈尔茨山之行给了歌德独特的宁静,使他暂时疏离人群,隔绝悲伤。对大自然的敬畏帮助他自我克服,自我超越。在山中的日子,他见识了自然的光影变幻,矿石的肌理质地,积雪的色彩魔力,歌德惊喜地发现自己具有成为一名地理学家、矿物学家和色彩学家的潜能。大自然为歌德提供了伟大教益,下山后的歌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歌德了。歌德怀着比以往更大的决心,投身于辅佐大公的使命,一大堆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任务也在等着他。“他天生就知道正确的前进方向,这种出色的能力伴随了他一生。”英国大诗人W.H.奥登这样评价歌德。
你若要建造一个美好的生活
就必须不为了过去而惆怅。
纵使你有一些东西失落,
你必须永久和新降生一样。
(冯至 译)

歌德《浮士德》插图,德拉克洛瓦绘
歌德活了83岁,在他那个时代,绝对是长寿之星。“群峰之巅,一片沉寂”,生命的杰作已然完成,孔夫子所言“尽善矣,尽美矣”,用来形容歌德的一生,实不为过。歌德创造了一个时代,并在他身后投下了长长的影子。我辈中人亦可以歌德为镜,自我修养,自我映照,在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奋进。
作者丨黄雪媛(太阳成集团tyc7111cc德语系教师)
来源丨文汇报